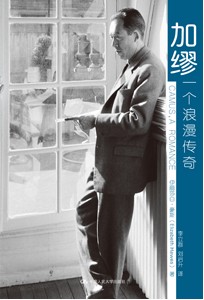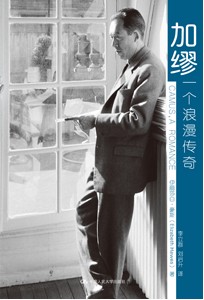
《加繆,一個(gè)浪漫傳奇》
作者:伊麗莎白·豪斯
出版:中國(guó)人民大學(xué)出版社 |
“但人們對(duì)自己的死亡是違心的,也與他們的環(huán)境相悖。人家對(duì)他們說(shuō):‘你會(huì)好的……’可他們還是死了。我不要這一套……我不愿說(shuō)假話,也不愿別人對(duì)我說(shuō)假話。我想將清醒保持到底,并以我全部的……(情感)來(lái)正視生命的結(jié)束。”
阿爾貝?加繆的名字很少出現(xiàn)在眾所周知的患有肺結(jié)核病的藝術(shù)家和作家的名單上——濟(jì)慈、雪萊、勃朗蒂姐妹、羅伯特?勃朗寧和伊麗莎白?勃朗寧夫婦、肖邦、契科夫、凱瑟琳?曼斯菲爾德、羅伯特?路易斯?史蒂文森。(還有西塞羅、帕格尼尼、盧梭、歌德、洛克、愛(ài)倫?坡、卡夫卡、華盛頓?歐文、D?H?勞倫斯、拉爾夫?瓦爾多?愛(ài)默生、喬治?奧威爾、史蒂芬?克萊恩、勞倫斯?斯特恩、西蒙娜?薇伊、安德烈?紀(jì)德——一直以來(lái),幾乎是不由自主地,我不斷搜集了解著這些曾備受肺結(jié)核病痛折磨的名人們的信息。)這表明,加繆成功地向外界隱瞞了他的真實(shí)病情,或者說(shuō)那場(chǎng)最終造成他死亡的戲劇性的車禍實(shí)際上使他的真實(shí)病情相形見(jiàn)絀。加繆患有嚴(yán)重的、不可治愈的肺結(jié)核病是毋庸置疑的。肺結(jié)核對(duì)加繆的生活和思想造成的根本性影響也是不可否認(rèn)的。他的疾病對(duì)他造成的改變遠(yuǎn)遠(yuǎn)勝過(guò)他曾遭受過(guò)的其他任何苦難——貧窮、沉默的母親、流亡他鄉(xiāng)——每一樣苦難都以各自的形式演繹著分離和放逐。正如他向朋友米歇爾?伽利瑪吐露自己17歲肺結(jié)核病發(fā)作對(duì)他造成的心靈創(chuàng)傷時(shí)所說(shuō),“恐懼足以解釋我變成了一個(gè)什么樣的人,到最后,最高貴的東西已不復(fù)存在。”
永遠(yuǎn)找不到一份關(guān)于加繆與肺結(jié)核病頑強(qiáng)抗?fàn)幍耐暾枋觥R驗(yàn)榧膊∈且患^(guò)于隱晦的事,而加繆的自我克制力又如此之強(qiáng)大。對(duì)于他的疾病,一直存在質(zhì)疑和爭(zhēng)議,不僅圍繞著他病情的嚴(yán)重程度和病痛的具體細(xì)節(jié),還涉及這種病的傳染性,尤其考慮到他曾與眾多女士有染。肺結(jié)核是一種通過(guò)空氣傳播的疾病,其感染率一般情況下為百分之五,所以,與加繆接觸的感染風(fēng)險(xiǎn)應(yīng)該很小,不過(guò),是否存在諸多影響他的疾病傳染程度的因素永遠(yuǎn)都不能為人所知了。加繆的朋友們對(duì)他的病情持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。據(jù)他的一個(gè)朋友說(shuō),加繆只是在淪陷期時(shí)病得很重;他的另一個(gè)朋友則說(shuō),在20世紀(jì)50年代初,“我們幾乎失去他。”伊曼紐爾?羅夫萊斯回憶他們的學(xué)生時(shí)代時(shí)說(shuō),那時(shí)大家都知道加繆感染了肺結(jié)核,雖然他很少提及。他只是周期性地從他們的視線中消失一段時(shí)間,然后再回來(lái),每次回來(lái)時(shí)都面色蒼白。讓?格勒尼埃,這個(gè)在加繆46年的生命中享受了30年的顧問(wèn)兼導(dǎo)師身份的特殊人物,談到了疾病對(duì)加繆性格造成的影響,認(rèn)為那或許能夠解釋成為“戰(zhàn)友”的加繆和成為“孤獨(dú)的偉人”的加繆。加繆的一對(duì)兒女從沒(méi)見(jiàn)過(guò)父親生病的樣子,因?yàn)樗幌胱屗麄兛吹剿牟B(tài)。而對(duì)同樣患有肺結(jié)核病的米歇爾?伽利瑪和凱斯特勒的女朋友馬曼因,他卻絲毫不隱瞞他的病情,總是和盤托出他們想要知道的任何信息。
除了頻繁的氣胸、各式各樣的替代療法和三十年里幾乎被一打醫(yī)生經(jīng)手過(guò)的治療,加繆的病例記錄相當(dāng)零散。盡管如此,透過(guò)這些點(diǎn)滴的細(xì)節(jié),用跟蹤調(diào)查和推理的方式,并通過(guò)了解肺結(jié)核治療發(fā)展的歷史,加繆患病后的生活還是可以變得越來(lái)越清晰。令人驚訝的是,當(dāng)我試圖將各種渠道的信息集合成一個(gè)完整的故事時(shí),加繆本人的貢獻(xiàn)居然如此有分量。在日記中,加繆可能不像凱瑟琳?曼斯菲爾德在她的許多筆記中表現(xiàn)的那樣情緒化,但是他描述了參軍被拒后所感到的羞辱,被禁止游泳后的痛苦,以及,盡管只有極少的幾次,肉體所遭受的禁錮和疼痛。“全神貫注奮力向山上走,空氣像燒紅的熨斗一樣灼燒著雙肺,或者說(shuō),像一片鋒利的剃刀切進(jìn)肺里,”他這樣寫(xiě)道,那時(shí)他剛剛步入20歲。(他還摘引了曼斯菲爾德的句子,這本身就像是一條有參考價(jià)值的參照注釋。)在寫(xiě)給信任的朋友們的信中,加繆如實(shí)坦白了他脆弱的健康狀況、他對(duì)于靜養(yǎng)的需要、舊病復(fù)發(fā)的悲痛和對(duì)臥床的厭惡。在給皮亞的信中,他寫(xiě)到自己拖著逐漸衰弱的身體生活下去的苦苦努力。1944年,加繆在勒龐內(nèi)里爾給一個(gè)身患肺結(jié)核病的朋友寫(xiě)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,信中說(shuō),他對(duì)康復(fù)已經(jīng)喪失了信心。
從很多方面來(lái)看,20世紀(jì)30年代中期,當(dāng)加繆在創(chuàng)作的時(shí)候,他積極的生活掩蓋了他的真實(shí)病情。每天都發(fā)生著那么多的事情,若非有時(shí)被迫中斷的旅游、強(qiáng)制的休息、胸部疼痛,以及在布拉格又一次對(duì)咯血事件的敘述,甚至讓人誤以為他的肺結(jié)核癥狀正在得到緩解。1935年加繆創(chuàng)作第一篇散文時(shí),他還是阿爾及爾大學(xué)哲學(xué)專業(yè)三年級(jí)的學(xué)生。他深入研究著他的同胞、來(lái)自于波尼的哲學(xué)家圣?奧古斯汀的哲學(xué)思想,為獲得高等教育文憑證書(shū)而撰寫(xiě)著論文,做著各種各樣的兼職工作,還剛剛陷入一場(chǎng)復(fù)雜的婚姻,同時(shí)為共產(chǎn)黨組織著一系列的政治和文化活動(dòng),此外,他還在知識(shí)界廣交朋友,不斷擴(kuò)大著自己的興趣愛(ài)好。他一度成為阿爾及爾年輕的花花公子,穿著時(shí)髦愛(ài)打扮,極為忙碌,也極為引人關(guān)注,是他那個(gè)圈子里的領(lǐng)袖人物。那一年的春天,他開(kāi)始記作家日記;第二年,他開(kāi)始創(chuàng)作他的第一部小說(shuō)《幸福的死亡》;接下來(lái)的一年里,又創(chuàng)作了《卡里古拉》和《西西弗神話》;然后是《局外人》。
然而,在忙碌的身影背后,疾病卻像一只巨大的黑手伸向了他,一連串的事件也因此受到了影響,并成為加繆未來(lái)生活必然的趨勢(shì):為投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主動(dòng)參軍被拒之門外,考取會(huì)士學(xué)位并在公共教育體系中從事教學(xué)職業(yè)的計(jì)劃被擱淺,最終還被迫離開(kāi)了阿爾及利亞。羅杰?基約認(rèn)為,疾病在加繆和第一任妻子西蒙之間的愛(ài)情上也扮演了一個(gè)奇怪的角色,并暗示說(shuō),他們兩人各自的缺陷——他的肺結(jié)核病,她的毒癮——將他們緊緊地束縛在一個(gè)彼此相互支撐的系統(tǒng)中,這個(gè)系統(tǒng)就像一個(gè)秘密的社會(huì)和一種救贖形式。基約解釋說(shuō),在他們分手很久之后,加繆還繼續(xù)給西蒙寄送關(guān)于治療和戒毒方面的書(shū)籍,但一直不留只言片語(yǔ),因?yàn)樗幌朐僖?jiàn)到她。“我有個(gè)印象,這段婚姻的失敗對(duì)他的生活造成的影響遠(yuǎn)比他愿意相信的更加巨大,”基約總結(jié)道。
對(duì)于他最好的朋友和病友米歇爾?伽利瑪,加繆則將他應(yīng)對(duì)肺結(jié)核病的辦法和盤托出。到米歇爾被發(fā)現(xiàn)感染肺結(jié)核的時(shí)候,加繆已經(jīng)有了16年的患病經(jīng)驗(yàn),他以一個(gè)老朋友和資深病友的身份給米歇爾寫(xiě)信,用戲謔和嘲笑的口吻勸說(shuō)米歇爾擺脫不斷加劇的憂郁情緒,但當(dāng)他傾吐關(guān)于生存的重要思想時(shí),會(huì)即刻變得嚴(yán)肅起來(lái)。他任意揮灑著信手拈來(lái)的黑色幽默,將它作為分散注意力的武器和防衛(wèi)機(jī)制,尤其是對(duì)那些同樣具有幽默感的朋友們。“由于幽閉恐懼癥,在飛機(jī)上略微昏厥了一段時(shí)間。但是,我還是順利著陸了,像雛菊一樣精神抖擻,”他向“偉大的圣人米歇爾”匯報(bào)著他的阿爾及利亞之行,后者正在瑞士里森的一家療養(yǎng)院里進(jìn)行為期8個(gè)月的臥床休養(yǎng)。那年冬天,加繆也回到布里昂松養(yǎng)病,但他仍然指導(dǎo)著米歇爾的治療,并花了三周的時(shí)間前去那家療養(yǎng)院看望米歇爾。幾年之后,亞尼娜和米歇爾反過(guò)來(lái)也經(jīng)常定期到卡布里看望加繆。這兩個(gè)男人都擅長(zhǎng)交友,他們友好、慷慨、忠心耿耿。他們還都喜歡大笑,曾并排坐在伽利瑪出版社的客廳里,展示著各自的骨灰盒,互相取笑。
沒(méi)有什么比分享一場(chǎng)威脅生命的疾病所帶來(lái)的焦慮更能使人緊密地團(tuán)結(jié)在一起——尼采把這種精神上的痛苦描述為因?qū)膊〉乃紤]而造成的折磨,認(rèn)為這樣的精神折磨可能超過(guò)了疾病本身所造成的肉體痛苦。到1947年,加繆早已克服了作為一個(gè)肺結(jié)核病人的最初恐懼,并作出了形而上的回應(yīng)。他將自己辛苦得來(lái)的經(jīng)驗(yàn)教訓(xùn)言傳身授給了米歇爾。米歇爾仍在里森療養(yǎng)時(shí),加繆在給他的信中談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“新生”。陀思妥耶夫斯基認(rèn)為,死亡最終將變得無(wú)關(guān)緊要。加繆將生病的體驗(yàn)與宗教體驗(yàn)相比較:
“即使你不信仰宗教,即使上帝死了(正像我的一個(gè)朋友所說(shuō),被人從身后暗殺的),但仍然有一些真實(shí)的東西存在于宗教經(jīng)驗(yàn)中,正如它們存在于簡(jiǎn)單的經(jīng)驗(yàn)中一樣,即個(gè)人生活與幸福最為疏遠(yuǎn)。”